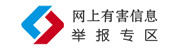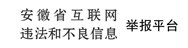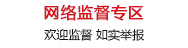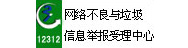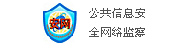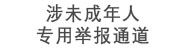黃梅戲誕生于田間地頭、村坊閭巷,在鄉(xiāng)間俚曲歌謠、燈會(huì)舞蹈的基礎(chǔ)上萌芽、孕育、成長(zhǎng),并演變?yōu)轵懵曋型獾闹麆》N,被譽(yù)為“中國(guó)最美鄉(xiāng)村音樂”。黃梅戲以其獨(dú)特的藝術(shù)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內(nèi)涵,成為中華戲曲大家庭中的一顆璀璨明珠,其形式特征、精神特質(zhì)和所扮演的文化角色,展現(xiàn)了長(zhǎng)江中下游流域的風(fēng)土人情和人文精神,傳遞了中華民族傳統(tǒng)美德和價(jià)值觀念,譜寫了當(dāng)?shù)厝嗣裆鎶^進(jìn)的史詩(shī)篇章。
探尋黃梅戲文化的歷史脈絡(luò)
在傳統(tǒng)戲曲界,歷來有“水路即戲路”的說法。黃梅戲在長(zhǎng)江中下游流域發(fā)端并展翼,發(fā)展成為橫跨數(shù)省的大劇種。作為成熟的、具有現(xiàn)代意義的劇種名稱,“黃梅戲”定名于 20世紀(jì)50年代。此前,曾有黃梅調(diào)、采茶調(diào)、花鼓戲、二高腔、皖劇、徽戲、懷腔或府調(diào)等別名,具有很強(qiáng)的自發(fā)性、隨意性和地域性。1953年,安徽省黃梅戲劇團(tuán)成立后,“黃梅戲”這一名稱迅速傳播到全國(guó)各地。
黃梅戲的萌芽,可追溯到流播于長(zhǎng)江中下游流域的采茶調(diào)。清中葉,傳統(tǒng)的采茶調(diào)與安慶地區(qū)的道情、花鼓、連廂、羅漢樁、送儺神、蓮花落等眾多民間藝術(shù)相結(jié)合,以唱為主的傳統(tǒng)民歌逐步演變?yōu)檩d歌載舞的民間小戲——“獨(dú)腳戲”“二小戲”“三小戲”。到同治、光緒時(shí)期,民間自發(fā)演出的黃梅小戲已經(jīng)在安慶鄉(xiāng)村頻繁出現(xiàn)。辛亥革命前后,當(dāng)時(shí)的省會(huì)安慶周邊出現(xiàn)了比較固定的班社,開始出現(xiàn)一批職業(yè)演唱黃梅戲的戲曲藝人。1926年,黃梅戲由民間草臺(tái)走向省會(huì)的城市舞臺(tái),不久后又向國(guó)際大都市上海進(jìn)發(fā),標(biāo)志著黃梅戲從農(nóng)民自?shī)首詷忿D(zhuǎn)向職業(yè)化演出,也昭示著黃梅戲的現(xiàn)代化轉(zhuǎn)型。在城市演出期間,黃梅戲接受了青陽(yáng)腔和徽調(diào)、高腔等親緣劇種的影響,擺脫了以曲唱為主的不成熟“小戲”狀態(tài),走上了集歌、舞、說白等綜合性舞臺(tái)表演的“真戲曲”之路。
新中國(guó)成立后,黃梅戲迎來第一次發(fā)展高潮。1952年11月,安徽省地方戲觀摩演出團(tuán)赴上海演出,嚴(yán)鳳英、王少舫等以清新質(zhì)樸的表演風(fēng)格、優(yōu)美動(dòng)人的唱腔轟動(dòng)上海,音樂家賀綠汀高度評(píng)價(jià)說,“在他們的演出中,我仿佛聞到了農(nóng)村中泥土的氣味,聞到了山花的芳香”,并邀請(qǐng)他們到上海音樂學(xué)院演出,黃梅戲開始走上繁榮之路。1955年,第一部黃梅戲電影《天仙配》上映,據(jù)1959年末統(tǒng)計(jì),該劇觀影人數(shù)高達(dá)1.4億人次,創(chuàng)造了中國(guó)戲曲電影史上的奇跡,也使黃梅戲由地方性小劇種真正影響全國(guó)、走向世界。黃梅戲由此成為安徽省最響亮的文化品牌和最具標(biāo)志性的劇種。
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(huì)后,黃梅戲迎來第二次發(fā)展高潮。借助電視這一新興傳播媒介走進(jìn)千家萬戶,黃梅戲躍升為全國(guó)五大劇種之一。從1982年黃梅戲電視劇《雙蓮記》大獲好評(píng)開始,《鄭小嬌》《女駙馬》《七仙女與董永》《小辭店》《潘張玉良》等眾多作品走進(jìn)熒屏,僅胡連翠導(dǎo)演的作品便10次榮獲中國(guó)電視劇“飛天獎(jiǎng)”、11次榮獲中國(guó)電視“金鷹獎(jiǎng)”,黃梅戲成為戲曲影視現(xiàn)象的引領(lǐng)者。安徽省確定“打好徽字牌,唱響黃梅戲,建設(shè)文化強(qiáng)省”戰(zhàn)略后,涌現(xiàn)出《秋千架》《風(fēng)雨麗人行》《柳暗花明》等新創(chuàng)劇目,特別是《徽州女人》自1999年首演以來,在大陸及港澳臺(tái)等地共演出600多場(chǎng),包攬了國(guó)內(nèi)各類戲曲大獎(jiǎng)。此間,湖北省政府實(shí)施“把黃梅戲請(qǐng)回娘家”文化戰(zhàn)略,黃梅戲在湖北省黃岡地區(qū)也萌發(fā)生機(jī)。
進(jìn)入21世紀(jì)的黃梅戲,入選首批國(guó)家級(jí)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名錄,在安徽、湖北兩省主導(dǎo)下穩(wěn)步向前。在全國(guó)文化體制改革中,安徽再芬黃梅文化藝術(shù)股份有限公司率先探索地方戲曲表演團(tuán)體的發(fā)展新路,被中宣部、文化部等授予“文化體制改革先進(jìn)單位”稱號(hào)。黃梅戲也在院團(tuán)改制后,創(chuàng)演了一大批集思想性、藝術(shù)性和時(shí)代性于一體的優(yōu)秀作品,如《鄧稼先》《鴨兒嫂》《不朽的驕楊》《東坡》《妹娃要過河》《六尺巷·寬》等。2010年,韓再芬應(yīng)邀訪美,其作品被美國(guó)國(guó)會(huì)圖書館永久收藏,成為中國(guó)戲曲歷史上第二位、新中國(guó)成立后第一位作品被收藏的戲曲表演藝術(shù)家;2013年,《女駙馬》在第六屆巴黎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戲曲節(jié)中榮獲最高獎(jiǎng)“評(píng)委會(huì)特別獎(jiǎng)”;2018年,《玉天仙》榮獲韓國(guó)戲劇節(jié)“最佳國(guó)際劇目獎(jiǎng)”;2019年,《薛郎歸》榮獲韓國(guó)光州和平國(guó)際藝術(shù)節(jié)“最佳劇目獎(jiǎng)”“最佳編劇獎(jiǎng)”“最佳演員獎(jiǎng)”。黃梅戲在國(guó)際舞臺(tái)上綻放出璀璨的光芒。
經(jīng)由田間地頭的鄉(xiāng)村小調(diào)到國(guó)際舞臺(tái)雅俗共賞的蛻變,黃梅戲不再僅僅是一種藝術(shù)形式,更是一種娛樂生活方式、一種深入人心的文化現(xiàn)象和區(qū)域文化標(biāo)識(shí)。
解碼黃梅戲文化的獨(dú)特魅力
廣義的黃梅戲文化是一個(gè)多層次、多維度的文化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,超越了單純的舞臺(tái)藝術(shù)形式,不僅涵蓋了與黃梅戲相關(guān)的物質(zhì)文化遺存和與之相關(guān)的歷史、民俗、精神傳承等方面的多維空間,還包括其在當(dāng)代社會(huì)中的多元化傳承、傳播與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所形成的各種新形態(tài)。其狹義內(nèi)涵聚焦于黃梅戲作為一種戲曲藝術(shù)形式的本體特征,包括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形式、表演體系、音樂唱腔、劇本文學(xué)以及傳承方式等核心要素。從廣義到狹義,黃梅戲文化既承載著鄉(xiāng)土社會(huì)的集體記憶,又凝結(jié)著舞臺(tái)藝術(shù)的核心精粹,成為中國(guó)戲曲藝術(shù)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連接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的文化橋梁。
黃梅戲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間性,是地域社會(huì)變遷和民眾生活的再現(xiàn),承載著農(nóng)耕文明的價(jià)值觀念與歷史記憶。黃梅戲生長(zhǎng)于長(zhǎng)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區(qū),深深扎根于源遠(yuǎn)流長(zhǎng)的農(nóng)耕文明。劇目?jī)?nèi)容多取材于當(dāng)?shù)氐臍v史故事、民間傳說和日常生活,反映了區(qū)域內(nèi)普通百姓的情感體驗(yàn)、價(jià)值觀念和生活智慧。藝人同時(shí)承擔(dān)著故事講述者、道德評(píng)判者、技藝傳授者的多重角色,通過戲曲表演,區(qū)域內(nèi)的歷史知識(shí)、倫理道德和生活技能得以傳承和普及。如《王小六打豆腐》對(duì)社會(huì)倫理和家庭倫理的闡述、《對(duì)花》對(duì)地域農(nóng)作物的描繪、《戲牡丹》對(duì)當(dāng)?shù)爻S弥胁菟幍慕榻B、《打豬草》對(duì)農(nóng)村飲食習(xí)俗的展示等。傳統(tǒng)黃梅戲雖然也關(guān)注“治國(guó)平天下”的大業(yè),但更關(guān)注鄉(xiāng)村的家長(zhǎng)里短和婚戀家庭等題材,更熱衷于表達(dá)基層的生存體驗(yàn)和訴求。即便是《天仙配》《女駙馬》等傳奇故事,也通過男耕女織、科舉赴考等情節(jié)構(gòu)建起農(nóng)耕文明的價(jià)值體系,人物情感熱烈奔放,體現(xiàn)出民間鮮活生動(dòng)的生命活力。黃梅戲進(jìn)城以后有逐漸雅化的傾向,但與正統(tǒng)的雅文化不同,雅化了的黃梅戲是俗中之雅,俗文化仍是其主導(dǎo)品格。
黃梅戲文化具有突出的開放性和包容性,能夠海納百川、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。如同長(zhǎng)江不捐細(xì)流而奔騰不息,黃梅戲文化對(duì)兄弟劇種和地域民間藝術(shù)形式兼容并蓄,綜合創(chuàng)新,形成了獨(dú)具特色的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。從早期向青陽(yáng)腔、徽劇移植本戲,到新中國(guó)成立后移植《春香傳》等朝鮮劇目,到新時(shí)期移植越劇《五女拜壽》、泗州戲《龍女》,到改編莎士比亞戲劇《無事生非》和經(jīng)典名作《紅樓夢(mèng)》《雷雨》等,移植、改編劇目一直是黃梅戲劇目的重要來源。黃梅戲聲腔的形成也吸納了親緣劇種的聲腔和其他民間說唱音樂,如仙腔源于道情,平詞、二行、三行來源于彈詞等。黃梅戲的伴奏初期僅以“三打七唱”的打擊樂器為主,隨后探索采用京胡托腔、二胡伴奏等,直到新中國(guó)成立后才逐漸確立高胡為主要伴奏樂器,改革開放以后又逐步構(gòu)建起以民族樂器為主、西洋樂器為輔的混合樂隊(duì)。又如,就傳播而言,當(dāng)多數(shù)劇種還囿于舞臺(tái)演出時(shí),黃梅戲已經(jīng)借助電影、廣播、電視等媒介,突破時(shí)空的限制走向海內(nèi)外。可以說,正是這種“集百家之長(zhǎng)成一家之言”的藝術(shù)品質(zhì),才使黃梅戲文化超越了狹隘的地域限制,獲得了廣泛的情感認(rèn)同。
唱響黃梅戲文化的時(shí)代新“聲”
2024年10月17日,習(xí)近平總書記考察安慶時(shí),強(qiáng)調(diào)要加強(qiáng)歷史文化保護(hù),堅(jiān)持創(chuàng)造性轉(zhuǎn)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,在發(fā)展社會(huì)主義先進(jìn)文化、弘揚(yáng)革命文化、傳承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上協(xié)同發(fā)力。深入貫徹落實(shí)習(xí)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,必須堅(jiān)持文藝“二為”方向和“雙百”方針,在保護(hù)好、傳承好黃梅戲文化的基礎(chǔ)上,推進(jìn)黃梅戲文化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。
全面保護(hù)好黃梅戲文化,夯實(shí)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根基。習(xí)近平總書記多次強(qiáng)調(diào):“保護(hù)好、傳承好歷史文化遺產(chǎn)是對(duì)歷史負(fù)責(zé)、對(duì)人民負(fù)責(zé)”,“歷史文化遺產(chǎn)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,不僅屬于我們這一代人,也屬于子孫萬代……守護(hù)好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(cái)富”。實(shí)現(xiàn)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復(fù)興,前提和基礎(chǔ)是要確立敬畏歷史、敬畏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意識(shí),全面加強(qiáng)對(duì)文化遺產(chǎn)的保護(hù)。黃梅戲在新中國(guó)成立前長(zhǎng)期受到主流社會(huì)的排斥,老祖宗遺留給我們的各類文化資料稀少且零散。當(dāng)前和今后一段時(shí)間,要做好黃梅戲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的深入挖掘、全面收集和系統(tǒng)整理工作,摸清家底、管好家業(yè),真正守護(hù)好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(cái)富。
全面?zhèn)鞒泻命S梅戲文化,激發(fā)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動(dòng)力。首先,要推動(dòng)黃梅戲藝術(shù)本體的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,在堅(jiān)守戲曲本體的基礎(chǔ)上,以黃梅戲藝術(shù)涵養(yǎng)時(shí)代精神,不斷在創(chuàng)作題材、藝術(shù)形式等方面開拓創(chuàng)新,以提升黃梅戲表現(xiàn)和融入當(dāng)代社會(huì)生活的能力和手段。其次,要強(qiáng)化黃梅戲的研究闡釋工作,對(duì)黃梅戲的發(fā)展歷程、表演風(fēng)格、藝術(shù)特色、發(fā)展規(guī)律等深入探索,系統(tǒng)構(gòu)建黃梅戲文化的理論體系、學(xué)術(shù)體系。再次,要拓展黃梅戲文化的傳播方式,借鑒與電影、電視聯(lián)姻的成功經(jīng)驗(yàn),積極融入當(dāng)前人工智能(AI)技術(shù)全面應(yīng)用于媒體領(lǐng)域的智媒時(shí)代,培養(yǎng)和擴(kuò)大黃梅戲的受眾群體,讓黃梅戲韻在現(xiàn)實(shí)社會(huì)和虛擬化的數(shù)字世界共存,使黃梅戲成為百姓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存在。
全面利用好黃梅戲文化,提升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效能。習(xí)近平總書記強(qiáng)調(diào):“要把歷史文化遺產(chǎn)保護(hù)放在第一位,同時(shí)要合理利用,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(wù)、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發(fā)揮作用。”要大力繁榮發(fā)展黃梅戲文化事業(yè),不斷完善黃梅戲公共文化服務(wù)體系建設(shè),提升文化服務(wù)質(zhì)量,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(zhǎng)的精神文化需求;積極擴(kuò)大黃梅戲的國(guó)際人文合作交流,提升黃梅戲文化國(guó)際影響力;強(qiáng)力推進(jìn)黃梅戲文化生態(tài)區(qū)建設(shè),全社會(huì)共同營(yíng)造豐富多元、活態(tài)存在的黃梅戲文化生態(tài)。堅(jiān)持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,通過深挖黃梅戲文化底蘊(yùn)、創(chuàng)新黃梅戲文化業(yè)態(tài)、塑造特色黃梅戲文化IP、開發(fā)黃梅戲文化創(chuàng)意產(chǎn)品等方式延長(zhǎng)黃梅戲文化產(chǎn)業(yè)鏈條,推動(dòng)黃梅戲文化和相關(guān)產(chǎn)業(yè)在更廣范圍、更深層次、更高水平上實(shí)現(xiàn)深度跨界融合,更加生動(dòng)地向人民講好“詩(shī)和遠(yuǎn)方”的故事,實(shí)現(xiàn)黃梅戲文化價(jià)值的溢出效應(yīng)。
正如習(xí)近平總書記所言,文物和文化遺產(chǎn)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,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中華優(yōu)秀文明資源。我們要積極推進(jìn)文物保護(hù)利用和文化遺產(chǎn)保護(hù)傳承,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產(chǎn)的多重價(jià)值,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、中國(guó)精神的價(jià)值符號(hào)和文化產(chǎn)品。新時(shí)代的黃梅戲文化工作者要堅(jiān)定文化自信,在守正創(chuàng)新上實(shí)現(xiàn)新作為,在培根鑄魂上展現(xiàn)新?lián)?dāng),續(xù)寫好長(zhǎng)江文化的戲曲史詩(shī),用黃梅戲文化講好安徽故事、傳播好中國(guó)聲音。
(作者單位:安徽省社科普及基地安慶師范大學(xué)黃梅戲藝術(shù)發(fā)展研究中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