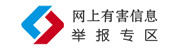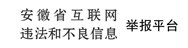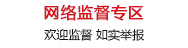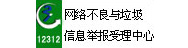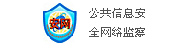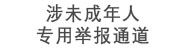春雨淅淅瀝瀝一潤,桐城的龍眠山就成了一塊浸了水的翡翠,滿眼都是流動的新綠。雨后天晴,山巒裹著一層薄霧,像一軸未干的龍眠山居水墨長卷,掛在小城的西北天陲,撩著游人邁開雙腿,一頭扎進薄霧里,近距離觸摸山水。
出城向西,穿過景區(qū)的標志性建筑“龍門”,便進入了龍眠山景區(qū)。沿頌嘉湖左岸繼續(xù)西行千余米,前方傳來隱約的轟鳴。繼續(xù)西行,轟鳴聲越來越響亮,如鼓點,從大地深處傳來,激越、雄渾、亢奮,敲得我心旌搖蕩。循聲右拐,沿坡道往忽皮嶺方向前行不遠,忽聞轟鳴的水聲自腳底的峽谷傳來。碾玉峽到了。
沿著下行的步道,踏上新架的橫跨溪流的拱橋。漲起的溪水經(jīng)過山地茶園間的溪道迎面而來,穿過拱橋一路歡歌,一如我歡快的心情。拱橋下方不遠處,水聲如安塞腰鼓,綿延不絕地敲在我的心坎上,我似乎感受到了空氣中微微的振動。
峽谷的南側(cè)又是一段傍山步道,一塊斜伸的山石擋住了一半去路,讓我不得不低下頭,放慢腳步。扶著步道的仿古欄桿,透過樹隙俯身望去,清澈的溪水自龍眠山上來,在眼前一塊突兀的巖石上跌宕。經(jīng)過時間的鏤刻和流水的剝蝕,巖石上露出一道道龜殼狀裂紋,圓潤卻又堅硬。水流經(jīng)此沖瀉,散發(fā)開來,形成白花花的瀑布,跌入水潭,稍作盤桓,便滑進一段狹長而幽深的峽谷溝槽,向著頌嘉湖蜿蜒而去。
峽谷的石壁上,刻有清代作家劉大櫆所作的《游碾玉峽記》。這里是龍眠山風景區(qū),山清水秀,景色宜人,文人墨客喜好游歷于此,留下諸多摩崖石刻。宋代畫家李公麟在這里繪《龍眠山莊圖》長卷,蘇軾為此畫題跋;明代大司馬孫晉引進珍稀的茶籽在這里種植,自此有了桐城小花茶;清代父子宰相張英、張廷玉晚年在這里歸隱,寄情山水。“水激而鳴,聲琮然,為跳珠噴玉之狀。又前行,稍平,乃卒歸于壑……”站在石壁前輕吟《游碾玉峽記》,字句間仿若傳來碾玉濺珠的錚錚回聲。
一處無名的亭子臨溪而立,翹角飛檐,當?shù)赜腥朔Q之為“觀瀑亭”。一塊巨大的天然石壩,嵌在亭下的溪谷里。清澈的溪水,從石壩的脊背上絲綢般滑過,以排山倒海之勢,跌入壩下的水潭,轟然間震得地動山搖。我不知道那塊石壩到底有多寬,它像一條座頭鯨,露出青灰色脊背,脊背北端嵌入峽谷陡峭的石壁。石壁被時光雕琢成一塊塊厚薄不均的石片,如一部部史書,又似數(shù)百年桐城文脈鐫刻的碑碣,記錄著文人墨客、史哲先賢流連龍眠山的腳印和足音。
“龍眠山中紫氣生,桐城小花勝龍井……茶葉滿筐如綠云,片片印著姑娘心。”思緒紛飛間,忽有山歌從山上傳來。抬眼望去,對岸大片青翠的茶園里,散布著一群穿紅著綠的采茶女,挎著篾簍,巧手如蝴蝶般在茶樹間上下翻飛,一邊掐著雀舌般的嫩芽,一邊唱起國家級非遺項目桐城歌中的《采茶歌》。那里是老姚茶莊的茶園,園主姚金芝正在組織春茶采摘。山上的茶園與山下的碾玉峽相互守望,地氣與文氣彼此成全。我不知道幾百年前劉大櫆踏春至此時,可曾聽見相似的歌謠,但我知道,碾玉峽不息的溪水里,早已氤氳著來自龍眠山上清新的茶香。
暮色降臨,峽谷里的景觀樓亮起暖黃色燈光,作為龍眠村2025年書記項目,樓內(nèi)展示的當?shù)靥厣r(nóng)產(chǎn)品也被燈光照亮。站在觀景臺前憑欄俯瞰,沿步道鋪設(shè)的夜燈如降落的星星,勾勒出棧道的輪廓,宛如潛伏的游龍,為夜游者舉起溫暖的火把,將游人的腳步和心頭照亮。倦鳥歸巢,山野漸靜,而水聲愈顯清越。我久久地佇立,恍惚間看到劉大櫆的青衫倒影與采茶女的藍布衣袂,在暖黃的燈光中若隱若現(xiàn),耳邊再次響起“水石相激,晝夜有聲”的回聲。
拾級回望,翹角飛檐的觀瀑亭像一位不離不棄的守望者,懸在峭壁間燭照清流。我知道,經(jīng)過幾百年光陰流轉(zhuǎn),碾玉峽晝夜不息的奔涌里,流淌的不只是一溪春水,更有古老文脈與鄉(xiāng)村蝶變的共振和鳴。